河套瓜果沁心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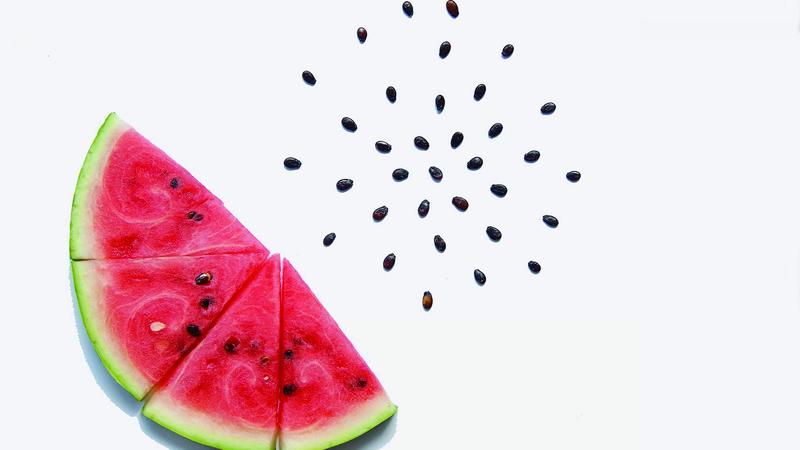

金色收获节节高 张桂林/摄
黄河水浸润的河套平原上,华莱士蜜瓜的琥珀色果肉裹着阳光流淌,西瓜在沙地里炸开红瓤的清响,鸡心果的酸甜在齿间蹦跳成儿时歌谣,西梅紫霜下藏着塞北的晚风。
这些土地孕育的甜,是经纬度赐予的糖分,更是游子梦里反复咀嚼的乡愁密码。
——编者
夏天的味道
□赵甜(磴口)
磴口的夏天是从华莱士瓜的香气里开始的。那香气先是若有若无地浮在空气里,像一缕游丝,待你凝神去嗅,却又消失不见。渐渐地,它变得浓郁起来,从巷口的瓜摊、从奶奶的蒲扇下、从每一个孩童的书包缝隙里钻出来,霸道地占据整个小镇的空气。我童年的暑假,总是和这种香气纠缠不清。那时候,每到七月中旬,家里就会买整编织袋的华莱士瓜,瓜皮上还沾着乌兰布和沙漠的细沙,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爷爷说,这瓜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所以特别甜。“小馋猫,别急。”爷爷总是这样笑着阻止迫不及待的我。他会先打一盆井水,把瓜浸在里面,冰凉的井水能让瓜肉更加脆爽。等待的时光最难熬,我蹲在水边,看着水面上倒映的自己,和那个金黄色的圆影一起摇晃。
终于可以吃了,爷爷的刀很利,轻轻一划,瓜就裂成两半。霎时间,一股混合着哈密瓜、苹果、梨等多种水果气味的复杂香气喷涌而出,填满了整个房间。瓜瓤是翡翠般的绿色,汁水顺着刀口往下淌,在桌面上汇成一小汪蜜糖。第一口总是最难忘的,牙齿陷入瓜肉的瞬间,先是感到一阵清凉,接着甜味像烟花一样在口腔里炸开。那不是白糖般单调的甜,而是带着花香果韵的甜,甜得丰富、甜得有层次。汁水多得从嘴角溢出来,赶紧用袖子擦,却还是把前襟也弄得黏乎乎的。那时候磴口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大棚,华莱士瓜只有盛夏才能吃到。为了延长这份甜蜜,姥姥会把吃剩的瓜皮收集起来,洗净切成细丝,拌上辣椒和醋,做成一道爽口的小菜。就连瓜子也不浪费,洗净晒干后,成为冬日火炉边最受欢迎的零食。
八月的一场暴雨过后,瓜季就接近尾声了,市场上的华莱士瓜开始变得稀少,价格也水涨船高。爷爷会买回几个,郑重地放在阴凉处,说要留到中秋节再吃。可往往等不到那天,我就禁不住诱惑,趁大人午睡时偷偷切开来吃。被发现后,免不了一顿训斥,但看到我嘴角残留的汁水,大人们又会忍不住笑出来。
如今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种包装精美的华莱士瓜,我却再吃不出当年的那种味道。也许缺的不是甜味,而是对华莱士瓜成熟的期待、是等待井水冰镇的耐心、是偷吃后被发现的紧张与窃喜。
去年夏天回磴口,正赶上第三十二届华莱士节,会场人山人海,舞台上吉祥物“磴瓜瓜”憨态可掬。我排队买了一颗华莱士瓜,坐在三盛公水利枢纽的堤岸上慢慢品尝。黄河水在脚下奔流,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也带着我童年的记忆,向东流去。瓜还是那么甜,甜得让人眼眶发热。我突然明白,华莱士瓜的味道,就是磴口人的乡愁。它金黄色的外表下,包裹着乌兰布和的阳光、黄河水的滋养,和一代代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河套西瓜消暑热
□运计彬(临河)
当夏日阳光热烈奔放地拥抱河套大地的时候,广袤无垠的绿野河川宛如大自然精心勾勒出的翡翠绿毯,那绿毯上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像绿宝石一样,仿佛在诉说着夏天的故事。
没有西瓜的夏天是无法想象的,没有西瓜陪伴的夏天更是没有灵魂的。酷暑难耐之际,信步碧绿的瓜园,仿佛置身于清爽的绿色世界。那些静卧在地、纹理清晰的“瓜宝宝”,仿佛大自然的宠儿。轻轻拍响它们,一股清凉迅即从指尖传递到心间,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在欢唱着丰收的喜悦。西瓜卧地清风拂,甜爽盈腔夏日怜,那鲜红的瓜瓤与甘爽的汁水沁人心脾,仿佛能将酷热、疲惫与烦恼一丝丝融化。
西瓜的前世今生
西瓜,只听名字就知道它来自西方。我国并非西瓜原产国,它原产于非洲干旱的热带沙漠地区,系葫芦科植物。《农政全书》中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西瓜一路漂洋过海传入我国,由于其甘甜清爽的口感和消暑解渴的功效,很快就成为人们喜爱的水果。1991年,西安东郊出土了一个唐三彩西瓜,说明西瓜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长安城,以它为模板制作陪葬器物,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西瓜的钟爱。到了明代,西瓜种植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使得西瓜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提升,在南北方各地广泛种植,成为夏季重要水果。我们喜闻乐见的冰镇西瓜,从明清时期就流行起来,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雷殿》中就记载了与友人浴后纳凉、携酒啜饮、浸食西瓜等生活细节,《红楼梦》中也数次提到贾府众人分食西瓜。近现代以来,西瓜的种植技术更加成熟,西瓜的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升。西瓜谐音“喜瓜”,所以也被赋予了吉祥圆满等寓意。
河套西瓜的由来与趣闻
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中国初无西瓜,洪忠宣使金,贬递阴山,得食之,其大如斗,绝甘冷,可治暑疾。”由此可知,阴山脚下的河套地区至少在宋代就开始种植西瓜了。抗战时期,一种名叫“地克森皇后”的西瓜在河套地区与当地西瓜混种,结出的果实被人们称为“混蔓瓜”。
河套地区七月中旬收割小麦,八月份开始打场。据父亲讲,过去打场虽然辛苦,但是中途休息时队里会给打场人挑来一大筐西瓜解暑。这时候,大家便会凑在一起,比一下眼力,看谁打开的西瓜好,猜猜西瓜是红瓤、白瓤还是黄瓤,是沙瓤瓜还是脆瓤瓜。有的挑瓜高手一弹就大抵知道了西瓜的瓤口,引得围观者啧啧称赞。大家对于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饶有兴致。过去的瓜只上点农家肥,所以个头普遍不大,但皮薄肉厚口感好,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真正的挑瓜高手并不是那些打场人,而是我们这些穿梭在瓜田的小家伙。麦熟之后也是西瓜成熟的时候,露水地的西瓜往往是最清爽甘甜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商量好,趁着早上露水还未散去,相约同去采瓜。用手一摸,瓜皮上没有露水、触感不冰的瓜都是熟好的瓜,此等摘瓜经验在儿时屡试不爽。炎热的晌午,西瓜的清爽实在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我们三五个小孩瞒着父母相约到金马湖畔耍水,耍完水又困又饿,就想着吃点什么。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瞄准村里的西瓜地,因为这时候看瓜的老大爷早已歇晌了。我们几个小家伙分工合作,蹑手蹑脚地趴在瓜地边的渠畔或玉米地里,观望着周围的情况。负责采瓜的小伙伴匍匐溜进瓜地里,挑一颗顶大的西瓜,然后使尽全身力气抱到地畔,接应的小伙伴接过瓜滚到玉米地或葵花地里。大家迫不及待地把瓜敲开,看着鲜红诱人的瓜瓤,也顾不上手上干净不干净,就开始大快朵颐,直至肚子圆鼓鼓的,左右摇晃还可以听到肚里水晃荡的声音。那弯弯曲曲的“小溪”顺着嘴角流过脖颈,浸湿了背心,弄得脖子和胸脯上到处都是。我们看着彼此的吃相,互相笑着打着饱嗝。
河套西瓜好吃,得益于河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吃法也可谓五花八门,连瓜皮都不放过,有凉拌西瓜皮、五花肉红烧西瓜皮、清炒西瓜皮、猪排炖风干西瓜条……一颗西瓜做出了不同花样。农忙之时,人们还会将熟透的西瓜一切两半,用勺子将瓜瓤挖出一小部分,挑出籽,再将厚烙饼掰成小块泡入其中,解渴又止饿,吃完之后继续耕作。
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优化,如今西瓜已经不是独属于夏天的水果。曾经的西瓜承载着大自然的慷慨给予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成为如歌岁月里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挂在枝头的美味
□白秀英(五原)
一
在美丽的河套平原,流传着一首民歌:“大佘太的葫芦,西水道的瓜,圐圙布伦的烟叶子人人夸……”歌词赞美了众多河套有名的土特产,而我今天要夸的是家乡那香甜诱人的水果。
河套地区不仅是闻名遐迩的“塞外粮仓”,也是久负盛名的瓜果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加上黄河水的滋养,培育出了众多可口瓜果。
在每年的八月底至九月中上旬,河套地区种植的法兰西西梅成熟了,它是河套水果界的后起之秀,惊艳亮相后,因独特口味受到人们的喜爱。第一次见到西梅,就被它的颜值圈粉:水滴形的果子肉鼓鼓的,非常娇憨可爱。它的个头比李子大,外皮颜色与李子相似,呈深紫色,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色果霜。剥下它的紫色外衣,便看到琥珀色的晶莹果肉。咬一口,汁水充盈、果肉嫩滑,吃后让人欲罢不能。西梅不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还可用于酿酒、制作果脯和饮料,多元价值让它成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河套的风,吹得瓜果香甜,也吹得农人展露笑颜。丰收时节走进西梅园,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丰盈的西梅挂满枝头,人们忙碌地穿梭于园间,摘果、运送、过秤、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而欢乐的景象。
河套人用最朴素的方式来种植西梅,不施化肥、不进行催熟,全靠自然生长。人工采摘分拣后还要经过两次筛选,尽可能地保证西梅的品质。河套西梅甜在心扉,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尝尝这挂在枝头的美味。
二
夏秋时节,大自然仿佛是慷慨的画家,它用缤纷的色彩和高雅的韵味,在广袤的河套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幅生动而丰富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那挂满枝头的鸡心果分外引人注目,它们宛如一颗颗小巧玲珑的红宝石,镶嵌在郁郁葱葱的绿叶之间,闪烁着诱人光芒。走近些,便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果香,清新而又甜美。
鸡心果是引进的新品种,又叫“塞外红”苹果,因颜色鲜红,外形是心形,所以被称为“鸡心果”,每年八月底至九月上旬成熟。它与苹果相似,但是口感比苹果脆甜,且营养更丰富。鸡心果不但具备丰产、快速回报等特点,而且符合市场需求,是广受欢迎的“金果果”。
阳春四月,鸡心果园内,葱绿的果树枝条上鸡心果萌出绿绿的小嫩叶,一簇簇的新绿叶长到一半时,便有青白色的花骨朵缀在绿叶间,不久就满树繁星了。这时果农们就会摘掉一些花骨朵,这样才能保障结果的质量。不久之后,一朵朵花儿蓬勃地露出了笑脸,五瓣的花儿娇艳欲滴、白中透粉。
进入盛夏,鸡心果渐渐成熟起来,青绿的果实染上淡淡的红晕,如少女羞涩的脸。等到夏天的尾声,鸡心果彻底熟透了,满树果实红彤彤的,似烈火燃烧,煞是好看。这时候,从树上摘几个鸡心果,在衣襟上蹭一蹭放入口中,酸酸甜甜的汁水涌进喉咙,幸福感缓缓流淌至心间,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细细品味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家乡的甜玉米
□池俊花(五原)
一说起玉米,舌尖上仿佛就泛起甜滋滋的味道,似乎每一个味蕾都装满了金黄的记忆,一个词一句话,就勾引得它们蠢蠢欲动,制造出充沛的口水。
玉米是我的偏爱,尤其是家乡的甜玉米,无论是黄玉米、白玉米,还是彩色玉米,我都喜欢。记得当初在乡下时,院子里有一块地,我把其中的一半用来分批次种玉米,每一批次种十几株。精心地松土施肥选种,然后把种子一粒粒种下,等到前一批种下的种子冒出鹅黄的小芽长到寸许,就开始种下一批。如此这般,当种最后一批的时候,第一批种下的玉米已经有尺把高,翠绿的衫裙已能随风摇曳了。看着眼前梯队形翠绿的苗阵,我开始掰着指头盼望秋风漫步河套平原的日子,仿佛能听到我眼前的苗儿们努力生长的声音,看到了苗株上孕育的一个个戴着红缨的嫩穗绽出甜蜜的笑靥,甚至都闻到空气里弥漫开来的浓浓甜香……
玉米的种子入土时,我总是格外虔诚。先是用锄头在松软的泥土上划出一道道整齐的沟壑,然后蹲下身,将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按进土里。种子入土的刹那,我总觉得它们在对我耳语:等着吧,我们会给你惊喜的。确实如此,不出三五日,泥土便会被一股力量顶开,冒出嫩黄的芽尖来。那芽尖先是怯生生的,继而便昂首挺胸,向着阳光伸展。我常常蹲在地头,看着这些新生命,竟能一看就是小半天。
玉米苗长到膝盖高时,便开始抽节。这时候,我总要给它们追一次肥。农家肥的气味虽不好闻,但想到这是玉米们最爱的营养,便也不觉得难闻了。施肥后的玉米仿佛获得了神奇的力量,一夜之间就能蹿高一大截。它们宽大的叶片在风中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常常坐在田埂上听这自然的乐章,直到暮色四合。一天天地看,一日日地盼,直到有玉米棒子长得丰满,顶上的红缨失了颜色渐趋枯黄,我就急不可耐地把它们掰下来,剥开外衣,只留下最里面一层米色的薄衫,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水,开煮。
煮玉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起初,锅里十分平静,渐渐地,水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泡,蒸汽从锅盖边缘钻出来,带着一丝甜香。再过一会儿,整个厨房都弥漫着玉米特有的香甜气息,那香气似乎有生命,会顺着门缝、窗缝溜出去,引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家在煮玉米了。揭开锅盖的那一刻最为美妙,蒸汽腾空而起,在氤氲的水汽中,玉米棒子金灿灿地躺在锅里,每一粒玉米都饱满得似乎要爆开。顾不得烫手,我总要抢先捞出一根,吹着气,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牙齿穿透薄薄的玉米皮,甜美的汁液立刻在口腔中迸溅,那种满足感,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
玉米的吃法多种多样,最原始的往往最美味。除了水煮,烤玉米也是我的最爱。将带皮的玉米埋在灶膛的热灰里,不多时,玉米皮就会被烤得焦黄,剥开来,里面的玉米粒金黄透亮,咬一口,外焦里嫩,还带着柴火特有的香气。有时候,我也会把玉米粒剥下来,和青椒一起炒,红绿黄相间,不仅好看,更是下饭的佳肴。
收获的季节里,玉米地是最热闹的地方。大人们忙着掰玉米,孩子们则在玉米秆间穿梭嬉戏。玉米秆高大茂密,成了我们捉迷藏的最佳场所。有时候玩累了,就随手掰一根嫩玉米,坐在地头啃起来。阳光透过玉米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就坐在这些光影里,享受着属于乡村孩子的简单快乐。玉米收获后,晾晒也是一道风景。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屋顶上都铺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在秋阳下闪闪发光。晒干的玉米粒可以磨成玉米面,做成窝窝头、玉米饼,那是冬日里暖胃的美食。而挑选出来的饱满种子,则被小心地收起来,等待来年春天再次投入大地的怀抱。
离开家乡多年,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玉米,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些玉米虽然个大饱满,却少了等待的美好,少了收获的喜悦。每次回老家,我总要到曾经种玉米的那块地看看。地还在,只是已经荒芜,长满了杂草。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玉米的甜香。
前些日子,姐姐寄来一包玉米面。打开包裹,那股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我用这些玉米面做了几个窝窝头,蒸熟后,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刹那间,童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清晨的露水、午后的蝉鸣、傍晚的炊烟,还有那一地摇曳的玉米秆……
原来,家乡的味道从未远去,它一直藏在我的味蕾深处,只消一口玉米,便能唤醒所有的记忆。那些关于玉米的往事,就像一粒粒金黄的玉米粒,串成了我生命中最甜蜜的念想。如今,每当我看到玉米,总会想起家乡那片土地,想起那些简单却充满期盼的日子。玉米于我,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连接我与故乡的纽带。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或许只有味觉的记忆最为恒久,它能穿越时空,让我们在异乡也能品到家的味道。家乡的甜玉米,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