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消失的沙漠》:沙退人进的奋斗长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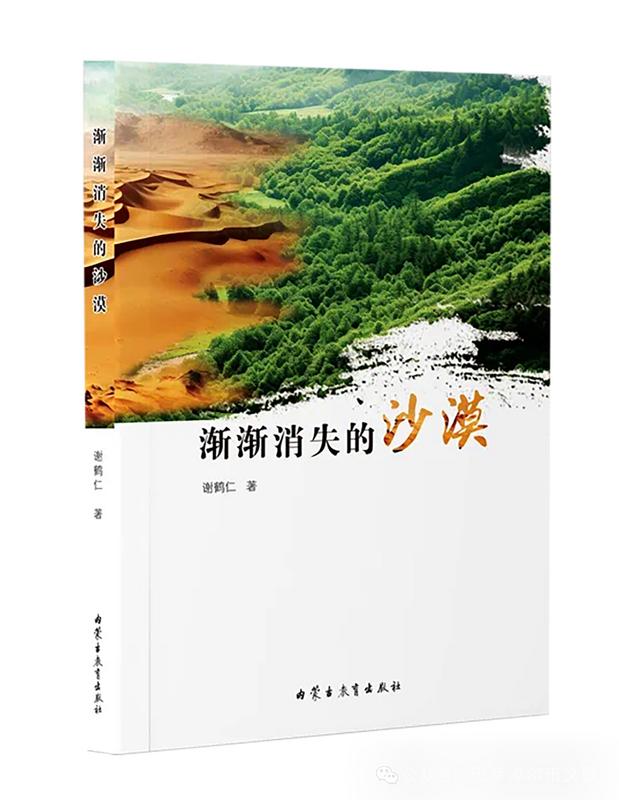
当黄沙节节败退,裸露的不仅是复绿奇迹,更是人们的坚持和付出。
纪实生态文学《渐渐消失的沙漠》讲述谢家人30年治理乌兰布和沙漠的感人事迹,让生态环保理念与奉献精神化作可触可感的生命温度,也折射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图景,是一曲沙退人进的奋斗长歌。
——编者
好大一棵树
——《渐渐消失的沙漠》读后
□张爱军(临河)
吃了豹子胆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六个月。在乌兰布和沙漠生活,哪个人的胃里没有二两沙?谢鹤仁就是以这样幽默风趣、生动形象的语言,写出一部十七万字的纪实生态文学作品《渐渐消失的沙漠》。该书讲述的是,他的父亲、“大漠愚公”——谢恭德,带领全家人治沙的故事。
《渐渐消失的沙漠》第一章节基本是纪实,把乌兰布和沙漠及磴口县的地理概况、来龙去脉,人口分布、生存现状等介绍得详详细细。而这不过是虚掩门缝,旁观侧立。从第二章节“家庭会”开始,谢鹤仁作为一个诗人的语言天赋显露出来了。
“大地像母亲的子宫,孕育出五谷,孕育出山川河流,也孕育出生老病死”“祝福的言语软绵绵的像一团毛线,再不像进树林放羊时的口气,一出口就横刀立马”……这些句子,似机缘巧合,欣然来到他笔下。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肚子吃饱了,随便在沙窝躺下展展腰,什么蓝天白云,什么理想人生,在这个时候都是浮云,我们的眼皮比锹头还重。”为了挖渠,父亲卖了一头猪,那是老农民一家人一年的油水;甚至背着老伴儿,把给大儿子娶媳妇儿的钱拿出来花了。“当时大哥二十五岁,我二十二岁,三弟二十岁。一家三个光棍儿子晃来晃去……”要是一个平庸的作者,接下来肯定会用大量篇幅去写父亲为治沙,是如何苦口婆心做母亲的工作,谢鹤仁没有,直接在第二段手腕一抖,写道:“他眉不秃,眼不瞎,找不到媳妇能怨我?”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外人面前,父亲是最讲道理的人。他在外头讲大道理,回到家讲小道理。
接下来一句:我们是父亲的三套马车。“五把锹并在一起,就是推土机”,把情节拉满,让读者的心紧绷起来。
谢鹤仁特别擅长对日常生活、劳动细节的描写和对人物内心思想斗争的捕捉,那自然是因为他太熟悉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说起他的苦豆坑,西沙窝、白茨圪蛋、开渠、栽树、种草、担土、甩锹,如数家珍。他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凭着“看沙子厉害,还是我厉害”的一股狠劲儿,“风啃不动石头,父亲就用石头挡树苗;石头没有了,父亲就捡起渠里挖出的红土结成的坷垃挡树苗;坷垃用完了,父亲就找酒瓶、穿破的鞋、穿烂的衣服、锄和锹等,只要能挡风沙什么东西都行。实在找不出快速压沙的宝贝,父亲就担红土来压”。从一开始的沙漠里种树,到最后树地里套沙,谢鹤仁没有故意拔高父亲的形象,只是将他日常的点点滴滴真实记录下来,不含“水分”。
纪实文学,既然称之为文学,就一定需要作家的艺术创造,结构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形成、化解等等。既不能违背自然写实的状态,“破坏生态”,也不能主观过强,用心过切,否则就成了“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一字不落地把过去发生的事儿如实记录下来,就又成了流水账,只能算是一种文字性资料,不能称其为文学作品。
苦难的名字是生活给的,就像乌兰布和的名字是风给的。栽树就得浇水。在高五米、宽五十米开外的沙漠中挖渠,可想而知。他写道:第一天,欢声笑语;第二天,少言寡语;第三天,不言不语。
“母亲看我们累成这样,为了节省体力,就把锅背进沙漠里做饭。我们在地上掏个窑,把锅放上去就是炉灶。沙蒿和白茨不缺,柴到处都是。面是母亲在家揉好的。由于没有烟囱,在揪面的时候,面被烟熏了,煮熟后发苦。这倒没什么,饥不择食嘛!吃完面,碗底会有一层沙。父亲说,在沙漠里居住的人不吃三斗沙土不叫大漠人。”母亲走后,他在纸上“讨伐”完父亲,又原谅了父亲。“我想,什么是根,根就是祖坟,父母去世后埋在哪里,我们的根就在哪里。”
本书在适当的场合加入了作者的一些诗作,起到烘托效果的同时,也让读者有了意外的收获。那些诗作铿锵有力,轻则取人泪水,重则动人魂魄。书中还运用了大量生活化的语言,比如“钱是硬头活气”“年年盼着年年富,年年穿着叉叉裤”等。其中有一句,我想大部分读者未必会在意,即“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保护神”。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在乌兰布和,梭梭就成了沙漠的保护神。然而,我却不愿这么轻轻地将它放过。以我对谢鹤仁的了解,这恰恰体现出他是一个内心有坚守、有信仰的人。
“我们偶尔也会喝酒,喝过酒的空瓶子在房后横躺竖卧着。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要是把酒瓶里灌满水,插进树苗,然后挖个深坑埋进土里,不知会怎么样?……树就活了,我把它称为‘酒瓶里的春天’。”
他活成了一棵树。
一位作家说: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自己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谢鹤仁的喉咙已经打开了,就待字正腔圆地唱下去。一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当你顺其自然时,磨不推自转。
生活无需虚构
——谢鹤仁《渐渐消失的沙漠》赏析
□何承刚(磴口)
5000亩的沙漠用肆虐的风沙埋压农田、村庄,逼迫村民由河西搬到河东,赖以生存的小河数次改道,年年清淤。一位倔强的老头带着家人进驻沙漠,靠一家之力,肩挑锹挖,背水浇灌,植树造林治理沙漠30年,让沙漠披上了绿装,彻底扭转了沙害局面。富有传奇性的是老头带领治沙的二儿子是一名诗人,作为主力参与了家庭治沙的全过程。
《渐渐消失的沙漠》的主人公,也就是父亲,叫谢恭德,被誉为“大漠愚公”“治沙英雄”;作者,也就是二儿子,叫谢鹤仁,是有一定名气的农民诗人。
一
感人的故事,加上作者的“在场”叙述,增强了这本书的带入感和感染力。
磴口县地处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与河套平原的接壤部,这里的人民生存一天,就要与沙漠抗争一天,或沙进人退,或人进沙退。磴口人一代接一代艰辛的治沙历程形成了可歌可泣的“治沙精神”。《渐渐消失的沙漠》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磴口县坝楞乡(后撤并)新河村。一条叫沈家河的小河南北向从村中穿过,河的东西两侧依据自然地貌形成了村落和农田。看似宁静的乡村图景却因为西部紧挨着沙漠而让这里的人们灾难重重:沈家河西侧的农田和村民的房屋被埋压,村民数次搬迁最终退守到河东,就连最后一道防线——沈家河也被风沙淤堵数次改道。
作品第一节的标题叫“清淤”,作者巧妙地从1984年河道清淤着笔,抓住了焦点,牵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开篇一首治沙背景诗后,第一句就是“1984年的春天,似乎比哪一年都来得早”,一下子牵动了读者的注意力——1984年的春天一定会发生什么。作者通过春种后一年一度的全县总动员开展河道清淤的大型劳动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沙给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沉重负担。也就是这一年,为了不让这种状况延续,谢恭德决定带领家人治理威胁村子正常生产生活的5000亩沙漠。在家庭会上,面对孩子们的反对声,他是这样说的:“不把沙子治住,河槽里的淤泥是你担还是我担?如果谁也不管,沙子从东风渠攻过来,我们怎么办?社员怎么办?”
河套是一个移民地区,谢恭德就是从民勤过来的移民之一。他来到新河村后,当过两任生产队长,带领群众开荒种田,拓展受沙漠困顿的有限耕地。
治沙需要巨大的投入,而谢恭德家里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还打着光棍,为此,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妻子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然而,任何困难都不能动摇谢恭德治理沙漠的决心。他住在沙漠里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土房里,“至此,父亲住在他大沙漠里简易的茅棚,不再回家。”他不仅把给大儿子娶媳妇的钱用在了治沙上,而且把专业打井的大儿子、当教师的二儿子、当木匠的三儿子以及正在上学的四儿子、五儿子都先后召集回来,用全部精力治理沙漠。
面对广袤的沙漠,一家人的力量杯水车薪,但一家人齐心协力不畏艰难的治沙精神是再大的沙漠、再肆虐的风沙也撼不动的。作品之所以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在于作者是在写自己流过的汗、流过的泪,甚至流过的血。如冒着风沙开挖引水渠、栽树,风沙将这些都埋了,就重复劳作;为了减少跑路,母亲把锅背到现场,埋锅造饭……一幕幕生动的场景触手可及,让读者和他们同喜同悲。又如描写沙漠里在县政府的支持下终于通电的情景:“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九年,这一天,我们盼了十六年,十六年来的每一个夜晚,父亲都是点着煤油灯度过的,看不上电视,只能听听收音机,废电池就有一箩筐。而村里,大部分人家,早把黑白电视换成大彩电了。”为了庆贺通电,一家人杀羊炖肉等待合闸灯亮,那种欢欣的场面让读者恨不得穿越过去和他们共享当时的欢乐。最后一句神来之笔:“这一晚,灯亮了一晚,谁也不敢去关灯,好像,灯一关,就再也不来(亮)了。”
对于老父亲带领家人治沙的壮举,作者不只是客观叙述,他是带着历史的眼光去回顾、总结、思考。作品的主线主要由这几个节点来贯穿:改造沙漠的艰难——成功后人们的嫉妒——60万的诱惑——“向县委送礼”。
这是一家极能吃苦的人家,却总是为钱所困,借钱成了他们的常态。深居沙窝的谢恭德凭着自己在村民中的威望,一户富裕的村民愿意借钱给他,但他却接受不了打欠条的要求,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时代在进步,生活在沙漠外的村民早已从电视上学到了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而生活在沙漠中的谢恭德却停留在过去,这两者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谢恭德因治沙功绩突出,成为媒体热捧、各级组织表彰的“治沙英雄”“大漠愚公”,还得到了一块“十佳致富能手”的奖牌,可他自己却无钱回老家祭祖团聚,女儿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对于这种“错位”,作者写道:“什么是英雄?英雄是什么?多少年后,我一个人在痛苦地回味着在默默思考着。”
由于沙漠的挤占,人们的生存空间非常局促,人均只有3亩地。沙漠横行肆虐的时候,人们躲避不及,老谢家治理成功后,一些人就得了红眼病,他们赶着羊去林地里放牧,挖甘草,甚至要集体瓜分治理后的沙漠。“比穷、比苦更大的灾难一天天向我们逼近。”“三弟因为阻止祝雄放羊,被祝家的秃手手打,被雷勇亮打;四弟阻止破坏植被,被王宏茹打;五弟被陈二颗头打、被雷勇打;大哥被黄电影打。”作者为阻挡侵占土地的推土机,腿被压在了履带下面。作者赞美了给予他们多方帮助的领导、群众以及淳朴乡风,但也对部分人愚昧、狭隘、自私、无知的劣根性给予了无情鞭挞,甚至对这种恶给予了因果的验证。
创业难,守业更难。就在一些人对林地虎视眈眈的时候,有商人愿意出60万元购买他们的5000亩沙漠。对于极度缺钱的谢家来说,这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窘境,由穷变富。可听到买家要在绿化的沙漠里搞养殖,谢恭德立马警觉起来:“原以为是来送蜂蜜的,没想到是送砒霜的……这是要毁掉我的植被。”
“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一号,党的生日这一天,六十八岁的父亲,要我陪他去给县委送礼。父亲的礼物有:
(1)一条一公里长的主渠道已经成形,不再受风沙侵扰;
(2)一条一公里的路可以行驶机动车;
(3)榆树,杨树,柳树,沙枣树,沙柳,红柳,成片不成片的有十七万株,沙笋,沙打旺,梭梭,沙拐枣,柠条,沙棘,这些新的物种实验成功;
(4)沙蒿,沙竹,沙芦草,沙盖,沙米这些野生植物开始存活;沙狐,野鸡,獾子不再稀奇——也就是说,由于植被的恢复,一切适应沙漠生长的生命渐渐茂盛,并呈现抬头趋势;
(5)一个约有十三亩地的果园挂果。
这是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十三口,十三年的劳动成果。”
上世纪的60万元真是一笔巨款,给儿子娶媳妇,给自己养老,改善其他子女的生活,总之可以解决他们当时的许多问题。但这笔钱没有打动谢恭德的心,他选择在党的生日这天,将一家十三口十三年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县委,献给党。一个高大的形象树立起来。谢恭德超乎常人的治沙动力曾经让人不解,此刻找到了答案。
二
非虚构文学在人物的塑造空间上有它的局限性,但如果能准确把握人物性格,通过言行、事件加以挖掘塑造,其非虚构的真实性更能打动人。《渐渐消失的沙漠》里面的人物塑造就比较成功,出现了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谢恭德首先是一个有明显保守传统观念的人,并且有严厉的家长作风。在开家庭会商量治理沙漠事宜,妻子因着急大儿子的婚事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时,“父亲感到的不仅仅是意外,而且颇为震惊,父亲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母亲从来就没有反对过父亲一次,母亲像是父亲的部分,附属品,或者是父亲的肢体或工具,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像圣旨、像铁板上钉钉……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父亲所决定了的事任何人只能服从不能反对,或者说,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绝对不可动摇。母亲更是父亲这种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无原则的、永远向着父亲,永远保持和父亲一致。母亲有时看见我和父亲发生争执,拿起笤帚就打我。”所以,这个家庭会其实是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父亲心里当然明白,开这个会,只表示,自己把自己的态度透露给三个儿子,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思想上有个准备,和母亲以及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说得更清楚些,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爷爷的爷爷还是这样。”作者对父亲的性格特点进行了生动的表述、准确的分析。正是有了这种性格基础和家庭地位,谢恭德才能“不近人情”地让自己的孩子一个个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奋战在沙漠里。
当然,谢恭德性格特点在作品中展现出的是多层次的、丰满的。他治理沙漠首先考虑的是改变村子的生态环境,消除沙漠的隐患,但也有个人的美好理想。当他们初进沙漠,建起简易的小茅屋时,“等不上自然干,父亲拾来了枯死的沙蒿、白茨天天烧,炕刚干了,门还没安,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搬进来了,搬进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父亲还在墙上贴了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看现在,雁落沙滩独自愁/望将来,鹏程万里卧群楼”,为自己治沙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
谢恭德虽然在家里有封建传统观念和家长作风,但在工作中并不保守。在两次担任生产队长时,他带领群众在沙漠中开荒种田,带头包产到户……只要是有利于村民的事情,他就敢干,显示出他有足够的魄力。
更可贵的是作品也表现了他柔情的一面:当妻子病重时,他一改往日的大男子主义形象,天天守在妻子身旁,关怀备至。妻子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依然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不让孩子们给穿老衣,安葬时坚持要为妻子披麻戴孝。这些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情节,让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性格特点,加上坚定的理想信念,“大漠愚公”的形象丰满地树立起来,让人感到可信、可敬、可亲。
林业局派下来指导谢家这个林业专业户种树的技术员闫茂林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闫茂林根本就不像个干部,他有时躺在父亲的小炕上看报纸,有时又给我们提耧种化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像个走亲戚的。”寥寥几句就把一个作风朴实、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干部活脱脱地表现出来。闫茂林为他们联系树苗,为谢家老三介绍了自己的侄女,为他们的困难奔走呼号。
作品中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性格泼辣的村民王兰,沙漠边上也有她的地,对偷牧行为不容分说,镰刀飞向羊群,骂声像机关枪射向放牧者,让读者解了一分气。
三
谢鹤仁作为有一定创作积累的诗人,作品中的语言体现出他一贯的特色:朴素、凝练,语句往往有诗歌的跳跃性和哲理性,形成想象的张力,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作品前言的第一句:“ 一棵树,就是佛龛前的一盏灯。一棵树的存在,就预示着有许多树也能生存,许许多多的树团结在一起,就能改变了一方水土。”这本身就是富有哲理的诗句。又如“ 苦难的名字是生活给的,就像乌兰布和的名字是风给的。如果不刮风的话,沙漠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们的渠就不会被沙掩埋,渠通畅,我们也不用浇一次水挖一次渠。”出于创作习惯,叙述中自然流露出诗化的语言。
在治沙过程中,谢鹤仁也一直用诗记录着他们创业的酸甜苦辣。因此,每当故事发展到关键节点,都会恰到好处地有一首诗加以烘托,让作者的情绪高蹈于激情的天空,形成强烈的感染力。母亲累死在沙漠后,悲痛的谢鹤仁用诗歌对父亲的“豪赌”进行了悲壮的宣泄:“沙漠的脾气/谁也拿捏不准/对付乌兰布和这头牛/草就是良药/父亲押上了全家/三年,沙打旺挑起了红灯笼/十年,喜鹊用鸟巢/倒画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二十年后,母亲像父亲的一滴泪/掉在沙漠/再也找不到了。”没有痛彻心扉的情绪体验,再高明的诗人也写不出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苦豆坑是他们治沙的核心地带,这里集中体现了他们所受的苦:“苦口的药/败火/败受风沙欺压的肝火/败不认命的怒火/治理苦豆湾/就得把苦难当成良药/装在苦豆湾这只大碗里/不去想,闭着眼睛捏着鼻子/我们一家三代二十一口人/咕嘟咕嘟往肚里灌/这药太苦了/母亲苦死了/父亲瘫了/妹妹腰上打了钢卡/四弟耳聋了/我的儿子和大侄女/初中/都没能毕业。”他把全家全部的苦凝练得苦不堪言,苦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作品的结尾,一首《愚公治沙——给父亲》,让读者在诗行里对父亲治沙乃至人生历程作了全面回顾,从心灵深处为伟大的灵魂唱响深情的挽歌。
谢鹤仁非常注重人物的语言特色,如父亲的民勤方言,王兰骂人的河套俗语,都用鲜明的语言特色衬托出人物的性格。
作品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下部的“丰碑”很大篇幅都是历年各类媒体新闻报道的简单整合,和上篇的承诺有分离感,没有形成全书统一的风格,但仍旧瑕不掩瑜。